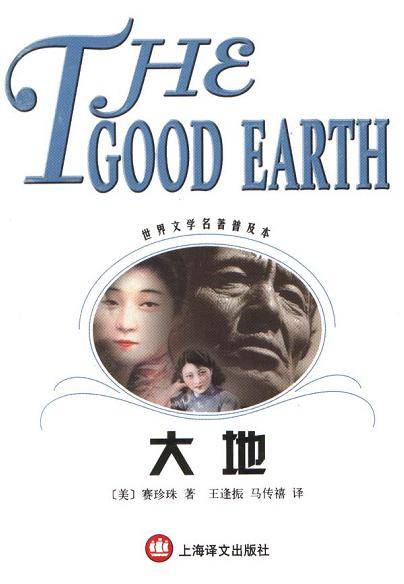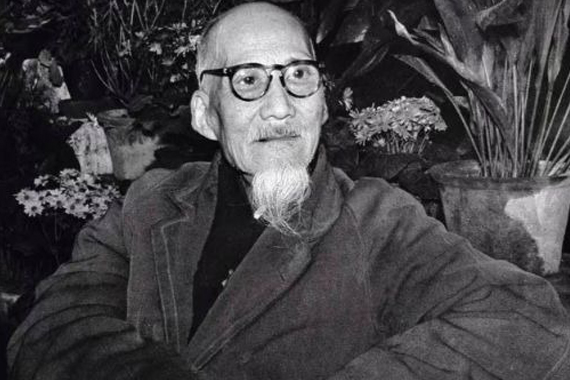-
大地 编辑
《大地》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创作的长篇小说,1931年首次发表。
《大地》以20世纪初的中国为背景,这一时期,许多农民主要靠土地维生。故事开始于男主人公王龙与女主人公阿兰的大婚之日,讲述了王龙一家人从一无所有到成为富农的故事。在《大地》里,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的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以饱蘸同情心的笔写出了“农民灵魂的几个侧面”。
在小说出版的20世纪上半叶,这一作品,跨越了东西文化间的鸿沟,有力改变了不少西方读者眼中中国那种“历史悠久而又软弱落后的神秘国度”印象。《大地》一经出版,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其独特的视角、优美的语言使该书连续两年稳居畅销榜冠军,并于1932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
作品名称:大地
外文名:The Good Earth
作者:赛珍珠
文学体裁:长篇小说
首版时间:1938年
字数:249000
小说叙述的是旧中国的农民王龙从一无所有而成为一个富户的故事。贫农王龙娶了一个大家庭的女佣阿兰做妻子。阿兰沉默寡言,吃苦耐劳,甚至在刚刚生完孩子后挣扎着爬起来和丈夫一起顶着烈日在田里劳作。但王龙嫌她不够美貌,对她十分冷淡。大饥荒来了,他们被迫举家前往南方谋生。王龙在一场动乱中浑水摸鱼发了财,靠着阿兰的帮助,回到家乡并买了许多田地,富裕起来。他愈发嫌弃发妻平庸的外貌,另娶了一个妓女。慢慢地,他老了,褪去了年轻时的浮躁和野心,惟一的心愿就是守住家业。他告诫儿子们千万不能卖地,土地才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孕育一切生命的基础。
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毁灭了中国的“天朝上国”之梦,更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撕裂得七零八落。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这成为近现代中国有识之士思考的核心问题。总体来说,在近代中国,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及如鲁迅这样的中间群体。尽管当时这些文化派别的观点错综复杂,文化价值取向南辕北辙。但是,他们都是站在一元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化之未来。幸运的是,在20世纪初期,有这样一位女性作家以独特的视角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她就是赛珍珠。赛珍珠的一生贯穿着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认知和传播这一主线。她曾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所以,她写作中国题材作品的根本意义在于,她要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
在赛珍珠拿起笔来写中国农民之前,她看到的类似美国文学作品中,中国人“总是拖发辫(不用说女的是缠小脚),挂鼻涕,佝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了窃盗、强奸、暗杀、毒谋等等看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举动”。而在《大地》中,中国人这一负面形象被彻底扭转。在这里看不到神秘的、不可理喻的人,中国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他们长年累月,抗争着天灾人祸,虽然身上有些固有的弱点和陋习,却更散发出人类普通成员所具有的人性光辉。
王龙
王龙保守落后,依附性强,理发师建议他剪掉城里人早已去掉的辫子,他却说:“没问我爹我可不能把辫子剪掉!”他重男轻女的子嗣观念强烈,妻子独自接生头胎孩子,他毫无体恤妻子之意,一个劲地追问是男是女。迷信思想不时干扰他的幸福。得了儿子,唯恐天上的精灵降灾,赶忙到土地庙烧香祈求保佑。欣赏儿子的漂亮,刚有得意之意,又担心被空中的妖魔妒忌,只好采取可笑的保护措施王龙可爱又可笑可敬又可悲的性格与心态不一而足。他虽愚昧无知,几近初民,可性格中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无原则的祖先崇拜、歧视女性的后天教养、渗入血液里的迷信观念与他强烈的生命冲动交织在一起,组成了这一人物性格的多元色调。
阿兰
《大地》这部小说塑造的阿兰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下受压迫的妇女形象。一方面,受西方进步女性主义思想影响,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阿兰依然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在父权制的夹缝中生存和抗争着。作品没有把阿兰仅仅描述成受害者和一个完全顺从于父权制社会结构下的女性,而是赋予了她主体地位,主动对父权制进行了抗争。阿兰是一位勇敢、坚韧、顽强、勤奋、能干并且富有主动进取精神的农村妇女。在艰难的环境里,她比王龙更聪明、更勇敢,经验更丰富、谋生方法更多,成了全家的精神支柱。阿兰不仅向父权制进行了抗争,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女人不仅可以照顾家庭,而且还可以参与家庭以外的事情,甚至可以比男性做得更加出色,展现了女性的强大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在《大地》中,赛珍珠虽然承认阿兰进行了抗争,而不是一味忍让、任人奴役,但也应该正确认识到阿兰的抗争是消极的,这就是由于她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只是从某些方面想要得到自己的权益,从没有想过从根本上彻底地去推翻社会中的男权统治地位。
主题
土地意识
在原始祖先的意识中,土地是人之所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大地》紧扣“土地”这一主题写出王龙的吃、住以及宗教信仰,无一不是来自土地。王龙的家中到处都是土地的意象,“房子是用从自家的地里挖出来的一大块一大块的泥土烧成的土砖砌成的,屋顶是用地里长出的麦秆和上地里的泥土盖成的,厨房是土砖砌成的。灶台也是祖父年青时用自家田里的泥土垒成的。年复一年,一日三餐做饭,灶台都烤焦烧黑了。”水缸是土烧成的,王龙焚香顶礼膜拜的土地爷、土地婆是田里的泥土塑成的。从王龙一出场到最后死去,与他的父亲、妻子一起,埋在他一辈子辛勤耕耘的田地里。赛珍珠清楚的意识到中国农民对土地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并突出表现为对“土地神”的信仰。主人公王龙的祖先在自家的土地上修建了小小的土地庙来祈求风调雨顺,他们虽然没有钱,但还是尽自己的可能把这个庙造得精美些,“两尊神像象是土地爷本人和土地婆。他们穿着用红纸和金纸做的衣服,土地爷还有用真毛做的稀疏下垂的胡须。每年过年时,王龙的父亲都买些红纸,细心地为这对神像剪贴新的衣服”,王龙对土地万分崇拜,极为虔诚,当遇到结婚、生子、收获时都要到土地庙去祭祀,在他看来土地神掌管着土地,也就掌握着他的命运。
土地是王龙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王龙知道,强盗小偷可以抢走和偷去他的银元和其他财产,但不能把田地夺走,他一有钱就置办土地。即使是在饥荒年代一家人濒临死亡,他宁愿南下乞讨,也决不卖田。当王龙的叔叔领着城里的投机商来乘火打劫廉价买地时,王龙愤怒地叫道:“我决不卖地,我要把田里的泥土,一块一块地挖起来给孩子们吃,等他们死了,我就把他们埋在田里,我和老婆,甚至我的老爹,我们都要死在这块给我们生命的田地上。”王龙明白,只要有田地在就还会有希望。离家南下逃荒,他望着田野上慢慢远去的人影,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道:“至少我还有田——我还有地。”在南方逃荒的日子里,王龙一家讨饭度日,受尽煎熬,王龙梦牵魂萦的还是故乡的田地,远离故土流浪乞讨决非长久之计,只有回到故乡自己的田地上才有希望。就在他准备忍痛卖掉小女儿筹钱回家之际,发生了贫民哄抢大户的事件,王龙意外地发了一笔财,他立即决定返回家园。回到家,看到桃树含苞欲放,柳树正要长出新枝,土地就要开种了,他浑身顿时充满力量,“好长一段时间,王龙似乎不想见任何人,只想单独和他的田地呆在一起。”王龙一踏进地里,他那强健的躯体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当连续七年丰收之后,一场大水淹没了王龙的大部分田地,他不能下地干活,与土地的联系被切断了,也就是在这时他平生第一次开始不满发妻阿兰曾经帮助他发家致富的那双大脚而迷恋上妓女的小脚,阿兰的脚象征着王龙与土地的脐带,一旦割断它,王龙便迷失了本性。洪水退去后,他欣喜若狂,大喊道:“锄头在哪里?犁在哪里?麦种在哪里,我要到田里去!”回到田里,王龙又有了笑声,“疲倦时,他躺在田地上睡大觉。大地的健康气息渗入他的肉里去,治愈了他的病。”赛珍珠活脱脱地表现出王龙这个中国农民与土地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结。
然而《大地》并不是单一地描写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大地》中提出了一个许多中国现代同类文学作品中所忽视的问题:一个极端贫困的农民有朝一日成为富甲一方的地主会怎样?在她的笔下,王龙这样的农民对土地的神秘信仰使他们形成了“靠天吃饭”的信赖性,七年的好收成,使他成为了富有的地主,然后洪水割断了他与土地的联系,无所事事的他也不能避免“温饱思淫欲”的魔圈,为了讨得爱妾荷花的欢心,他开始讲究穿戴打扮,头涂发蜡,为了去掉荷花讨厌的大葱味,他开始刷牙,甚至剪掉辫子,把与他甘苦与共,为他生男育女的发妻冷落在一边,开始挥霍享乐。这时的王龙俨然抛弃了农民的身份,过上了黄家地主那样淫逸放浪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背后留给他的是无尽的空虚。王龙和两个儿子在田里散步时,突然听到两个儿子商量着要把田卖,王龙喊道:“啊,游手好闲的孽子——卖田!”他禁不住声音嘶哑、破碎,愤怒得一口气上不来,就要栽倒,两个儿子赶忙扶住他。“开始卖田地一家子就完了,”“我们来自大地,我们也必须回归大地——如果你们守住田地,你们就能活下去——没有人能抢走你们的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他们努力劳作是为了在现世过上好的生活,这与西方重视救赎重视来世的文化价值观是不同的,所以赛珍珠十分理解王龙这样的中国农民,在书中不止一次地为王龙辩护“地主也不好当啊”。然而当时许多评论者过分注重赛珍珠对王龙地主生活的描写,认为赛珍珠是在丑化中国人的脸谱,是在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仔细阅读《大地》文本,赛珍珠并没有刻意丑化中国农民,无论是写王龙的传统美德也好,传统痼疾也罢,她都是在力求表现当时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以及中国农民的真实心态。
《大地》真实地去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状态,将真实的中国传播给世界的理想。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腐朽的,甚至有人希望它从此消失在世界文化之林,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熏陶的赛珍珠却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闪光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它拒绝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流,为了打破这种文化壁垒就必须找到二者之间的共性。土地是人类文化的典型代表和重要载体,它承载了人类热爱生命、尊崇道德、的集体无意识,沉淀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长河之中。对土地的探究,是洞悉人类文学、文化内在精神的一个极佳切入点,土地积淀着人类文化的伦理感情,土地是人的“根”,人的归宿,人的价值之本,人的善的本源。中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土地成为安身立命之基,农民与土地有着最直接联系,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普遍成员,他们将浓浓的土地情结内化对自然的依恋、对故园的眷顾之情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气质和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因而《大地》中紧紧地抓住了“恋土”这一人类共通的情感,塑造了王龙这样一个与土地有着生死关系的农民形象,从王龙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古希腊神话中阿尔库俄纽斯的影子,他们都离不开土地,阿尔库俄纽斯从土地母亲那儿获得永不枯竭的力量,王龙则能过在土地上劳动表达对大地的敬重。离开土地,王龙也如同阿尔库俄纽斯那样失去了生命的色彩。法国的狄德罗曾说:“人离开了土地就一文不值”,而重新寻找到道德信念的出路便在于回归土地,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依托与归宿,断裂和破碎的心灵世界才能复归完美与和谐,所以“我们来自大地,我们也必须回归大地——如果你们守住田地,你们就能活下去。”
文化融合
《大地》以王龙一家人的生活为主线,以女主人公阿兰为主体,塑造了全新的、有血有肉的中国农民形象。赛珍珠运用中国人的视角,以文化为切入点,描写中国农村和城镇生活,向西方阐释中国;以土地为纽带,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站在两种文化的交叉面上,既看到了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对立,又看到了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大地》站在了人类共性的高度,承认文化是多元的,不应该存在哪种文化强势就要独霸天下,哪种文化处于弱势就该全盘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并站在文化平等的基石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在交流与对话中求同存异,共生共融。
总的看来,赛珍珠的文化思想同泰戈尔、罗素等人有一脉相承的地方——都是在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面前,依旧鼓吹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必然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构成尖锐的矛盾并产生激烈的思想交锋。但是,对于一些中国本土作家而言,渐渐地察觉到赛珍珠盲目固守土地思想的种种弊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中,广大中国农民依靠在土地上的艰辛劳动,不但不能改变贫穷挨饿的悲惨命运,反而会摧毁农民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变得越来越愚昧和麻木。因此,他们支持和鼓励农民起来通过武装暴动来推翻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实现农民的解放,而这在赛珍珠那里是绝对不允许的,甚至是严厉批判的。赛珍珠写作的目的是想真实地再现中国当时的客观现实,是想向西方如实地介绍中国。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地出现。”她要借助笔墨文字把中国普通百姓的勤劳善良、喜怒哀乐真实地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从而更好地实现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手法
文笔
《大地》文本中散于各处的时间节点:开篇便是“这天是王龙结婚的日子”,直奔人物一生中关键的一天,“小说一开始就像是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迷人的风俗画,主人公穷困潦倒,但阅读时我们并没有为之心酸,而是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也有专家认为此处“颇有些《三国演义》开篇‘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意味’”;烘托喜庆气氛的一句“春天来了⋯⋯;“孩子生下的第二天,阿兰就起床了,照常给他们做饭⋯⋯”,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却映照了阿兰辛苦艰难的一生;“当冬天凛冽刺骨的寒风从东北方的荒漠地带吹来时,他们安坐在家里,周围是一片富裕的景象”。冬天里王龙家的兴旺情景象征着娶了阿兰之后日子的改善,是这户农家上升阶段的标志。而这种上升的另一个标志便是王龙买了地主家的地,去看地的日子是“在新年二月里的一个阴天”,这样的时间概念颇值得品味,新年二月,是新的开始,好的兆头,偏又是个阴天,这里已经为王龙家族的兴衰埋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
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在赛珍珠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王龙一家的日常琐碎,被这些极富口语色彩的时间节点巧妙地连接到了一起,零碎却不散乱,事多却很有序,看似无心写就,实则有意为之,首部曲中主要表现了王龙的生活场景,而作为一个农民的王龙,作为一个视土地为命的王龙,他的生活就是零零碎碎,日复一日,碎散的时间节点拼凑了王龙的一生,也拼就了首部曲的脉络。
人物形象
赛珍珠为王龙的庸碌一生感到倦怠,特意为他补充了阿兰这样一个人物,寡言少语,辛苦一生的阿兰并未占去多少笔墨,正如她在王龙家的地位一样,做着辛苦的活,享着最少的福。乍看之下,阿兰的人生在《大地》中并非浓墨重彩,但字里行间,特别是赛珍珠有意无意地牵来往日的时间之维,将读者的视线立体化,将阿兰的悲苦一生作昙花一现,最典型的一处便是当阿兰领着孩子们在街头行乞时,王龙和孩子们对阿兰自然而然、无师自通的乞讨声感到惊讶,阿兰却平静地说到“我小时候这样讨过,而且讨得到。那年也是这样的荒年,我被卖去做了丫头”。王龙和孩子们的惊讶与阿兰的平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对比之中,在阿兰“小时候”的一言带过中,读者仿佛看见了时间的闪回,刹那之间,便看尽阿兰从前的种种辛酸。这样的时间闪回并非无足轻重,因为正是这样的闪回,拓展了文本的厚度与深度,使得无限深意蕴于文字之外。“正是由于赛珍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妇女的了解,以及她娴熟的运用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才使得阿兰成为《大地》中的经典人物,也使得《大地》这部作品更为厚重。”在以王龙的人生为主维的《大地》首部曲中,阿兰的人生与王龙的人生自结婚之日起出现交集,并相互糅合在一起,使得王龙粗放庸碌的生命之中,呈现出一丝细腻与温情。
叙事时间
一幅上佳的绣品,除了要有好的轮廓,还须有精密的针脚,写作亦是如此,宏大主线框架之内,还得有丰富的内容来使之丰满。没有明确的纪年的《大地》,时间之维的踪影散见于文本各处,看似不经意间,岁月的痕迹已跃然纸上⋯⋯如此叙事效果得益于赛珍珠叙事中口语化的时间节点的大量灵活应用,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
赛珍珠别具匠心地将源置于时间之维的交集漩涡之中,通过源的眼睛,将匆匆前行的时间的痕迹深深刻下,将往日乡村曾经有过的片刻宁静再现,又用风起云涌的革命号角吹破这交错混乱的时空;通过源的思考,将几代人的梦想与困惑一一展现。
《大地》(The Good Earth)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的诺贝尔奖获奖著作。
在小说出版的20世纪上半叶,作品跨越了东西文化间当时存在的巨大鸿沟,有力地改变了不少西方读者眼中中国那种“历史悠久而又软弱落后的神秘国度”印象,客观地促进了东西文化的沟通。
小说1931年一问世,就在处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让他们看到中国农民兄弟身上所表现出的顽强的生存意志力。可以说,《大地》通过对中国形象更加实际的塑造,以及对中国人自身新的、更亲切、更有感染力的描写,取代了大多数美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在美国文学评论界受到冷遇的著作《大地》,却被大众英语读者奉为“经典”,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作品推荐体系和传播途径。
《星期六文学评论》称《大地》是“一部非常优美、非常优美的小说。我们终于从一部小说的字里行间读到真实的中国人民,我们在书中看到的不是人们经常描述的荒诞无稽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是诚实的农民、忠诚的妻子,富饶的大地、农民的泥土房,布克夫人的小说是如此感人,如此真实”。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赛珍珠女士,你通过那些具有高超艺术品质的文学著作,使西方世界对于人类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你赋予了我们西方人某种中国精神,使我们认识和感受到那些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情感,而正是这样的思想情感,才把我们大家作为人类在这地球上连接在一起。”
 赛珍珠
赛珍珠
1、本站所有文本、信息、视频文件等,仅代表本站观点或作者本人观点,请网友谨慎参考使用。
2、本站信息均为作者提供和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
3、对任何由于使用本站内容而引起的诉讼、纠纷,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有侵犯你版权的,请来信(邮箱:baike52199@gmail.com)指出,核实后,本站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