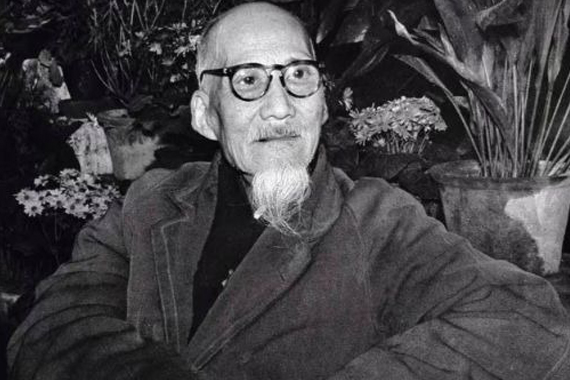-
西尔维娅·普拉斯 编辑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年10月27日—1963年2月11日),美国自白派诗人的代表,是继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1963年她最后一次自杀成功时,年仅31岁。这位颇受争议的女诗人因其富于激情和创造力的重要诗篇留名于世,又因其与另一位英国诗人特德·休斯情感变故自杀的戏剧化人生而成为英美文学界一个长久的话题。
中文名:西尔维娅·普拉斯
外文名:Sylvia Plath
国籍:美国
出生地: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出生日期:1932年10月27日
逝世日期:1963年02月11日
职业:诗人
代表作品:《巨人及其他诗歌》
当母亲告诉她父亲的死讯时,她决然地说:“我不再与上帝通话了”。之后,她不断在诗中歌吟死亡,也曾多次试图自杀:“死去是一种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善此道”。“我又做了一次/每十年当中/我要安排此事”。“看,黑暗从爆裂中渗出/我不能容纳这些,我容不了我的生命”。“从灰烬中/我披着红发升起/像呼吸空气般地吞噬男人”,“像猫一样可死九次”。“这女子已臻于完美/她死去的/身体带着成就的微笑”。
在大学期间她学业出众,每门功课都是优等,获得多项奖学金。大学二年级时因出色的写作才能被纽约时装杂志《小姐》选中应邀担任该杂志的客座编辑。不久她就陷入在精神分裂的磨难中,直至进入麦克林精神病院被进行电疗。她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就是描写这一段经历。
1955年,普拉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于1956年2月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准去英国剑桥留学。她在那里邂逅了英国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1930—1998),两人立刻坠入了情网,于1956年6月结婚。普拉斯与休斯育有一子一女。
当时普拉斯称休斯为“世间惟一能与我匹配的男子”。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1962年9月普拉斯与休斯分居,她单独带着儿女在伦敦居住。同年休斯与Assia Wevill同居。普拉斯在数月内突然面临的剧烈的生活变动,以及生活拮据所带来的压力,《钟形罩》刚刚出版却反映平平,与休斯办理离婚手续过程中承受的巨大的精神痛苦,促使她再一次地选择了自杀。1963年2月11日,她在伦敦的寓所自杀。
 普拉斯之墓
普拉斯之墓
普拉斯的小说创作有非常突出的自传性特色,几乎每一篇都能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中找到影子。作为诗人的普拉斯也曾非常投入地学习过绘画,这些特点都鲜明地体现在本小辑所选的这几个短篇中:感情细致入微,用词不俗而且准确,描摹景物富于色彩感,因此赋予她的小说一种独特的阅读快感。《绿石头》是对童年生活令人怅惘的追忆;《超人与宝拉·布朗的新冬装》叙述的是成长经历;《寡妇曼加达其人》根据作者新婚后去西班牙度假的经历写成,体现了过人的观察能力;《成功之日》记录了一对献身写作的夫妇的生活及妻子微妙的心理活动,联想到普拉斯本人,读来令人感慨。
她的部分著名诗歌有:《十一月的信》《雾中羊》《邮差》《榆树:作为悔悟的幻想之光》《语言》《爱丽尔》《边缘》《晨歌》《穿黑衣的人》《词语》《冬天的树》《渡湖》《对手》《巨像》《慕尼黑女模特》《你是》《十月里罂粟花》等等。
小小的罂粟花,小小的地狱之火,
你不伤人?
你闪烁不定,我不能碰你,
我把双手伸进火中,什么也没燃烧,
瞧着你那样闪烁我感到
绵绵无力,多皱,鲜红,就像人的嘴唇,
刚刚流过血的嘴唇。
血淋淋的小裙子!
有些烟味我不能闻,
你的鸦片和你令人作呕的容器在何处?
但愿我能流血,或者入睡!──
但愿我的嘴唇能嫁给那样的创伤!
或者你的汁液渗向我,在这玻璃容器里,
使人迟钝,平静,
可它是无色的,无色的。
《申请人》(赵毅衡译)
首先,你是否我们同类?
你戴不戴
玻璃眼珠?假牙?拐杖?
背带?钩扣?
橡皮乳房?橡皮胯部?
还是仅仅缝合,没有补上缺失?没有?没有?
那么我们能否设法给你一件?
别哭,
伸开手。
空的?空的。这是只手,
正好补上。它愿意
端来茶杯,揉走头痛,
你要它干什么它都干。
你愿意娶它吗?
保用保修
它临终时为你翻下眼睑,
溶解忧愁。
我们用盐制成新产品。
我注意到你赤身裸体,
你看这套衣服如何──
黑色,有点硬,但挺合身,
你愿意娶它吗?
不透水,打不碎,
防火,防穿透屋顶的炸弹,
你放心,保证你入土时也穿这衣服。
现在看看你的头,请原谅,空的。
我有张票子可供你选用。
来啊,小乖乖,从柜子里出来,
怎么样,你看如何?
开始时象一张纸般一无所有,
二十五年变成银的,
五十年变成金的。
一个活玩偶,随你怎么端详。
会缝纫,会烹调,
还会说话,说话,说话。
很派用场,不出差错。
你有个伤口,它就是敷药,
你有个眼睛,它就是形象。
小伙子,这可是最后一招。
你可愿意娶它。娶它。娶它。
《边缘》(赵琼、岛子译)
这个女人尽善尽美了,
她的死
尸体带着圆满的微笑,
一种希腊式的悲剧结局
在她长裙的褶缝上幻现
她赤裸的
双脚像是在诉说
我们来自远方,现在到站了,
每一个死去的孩子都蜷缩着,像一窝白蛇
各自有一个小小的
早已空荡荡的牛奶罐
它把他们
搂进怀抱,就像玫瑰花
合上花瓣,在花园里
僵冷,死之光
从甜美、纵深的喉管里溢出芬芳。
月亮已无哀可悲,
从她的骨缝射出凝睇。
它已习惯于这种事情。
黑色长裙缓缓拖拽,悉悉作响。
《巨神像》(张芬龄、陈黎译)
我再也无法将你拼凑完整了,
补缀,粘附,加上适度的接合。
驴鸣,猪叫和猥亵的爆裂声
自你的巨唇发出。
这比谷仓旁的空地还要槽糕。
或许你以神喻自许,
死者或神祉或某某人的代言人。
三十年来我劳苦地
将淤泥自你的喉际铲除。
我不见得聪明多少。
提着镕胶锅和消毒药水攀上梯级
我像只戴孝的蚂蚁匍匐于
你莠草蔓生的眉上
去修补那辽阔无比的金属脑壳,清洁
你那光秃泛白古墓般的眼睛。
自奥瑞提亚衍生出的蓝空
在我们的头顶弯成拱形。噢,父啊,你独自一人
充沛古老如罗马市集。
我在黑丝柏的山巅打开午餐。
你凹槽的骨骼和莨苕的头发,对着
地平线,凌乱散置于古老的无政府状态里。
那得需要比雷电强悍的重击
才能创造出如此的废墟。
好些夜晚,我蹲踞在你左耳的
丰饶之角,远离风声。
数着朱红和深紫的星星。
太阳自你舌柱下升起。
我的岁月委身于阴影。
我不再凝神倾听龙骨的轧轹声
在码头空茫的石上。
《爱丽儿》(1)(戴珏译)
黑暗中凝止。
然后是无质的蓝
山岗与距离的流驶。
上帝的母狮,
我们变得如此一体,
脚跟和膝盖的支点!──犁沟
分裂、掠过,与我无法
抓住的脖子
的棕色弧形类似,
黑奴眼
莓果抛出深色的
钩子──
一口口黑色鲜甜的血,
一片片阴影。
另有东西
把我在空中拖过──
双股,毛发;
我脚跟的碎皮。
白色的
戈黛娃(2),我剥掉外皮──
死去的手,死去的严苛。
而现在我
对着麦子吐泡沫,海浪的闪光。
小孩的哭喊
在墙里融化。
而我
是那支箭,
与那飞溅、自毁的
露水,有着一致的冲劲
飞进那红色的
眼,黎明的大锅。
注:
(1)爱丽儿可能指作者常骑的一匹马。莎士比亚《暴风雨》剧中有个精灵也叫爱丽儿,因曾被一位魔法师所救而成了他的奴隶,在完成魔法师布置的一系列任务后最终获得了自由。另外在希伯来语中,爱丽儿的意思是“上帝之狮”,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个词可能也像圣经以赛亚书中那样象征耶路撒冷。
(2)戈黛娃指十一世纪英格兰的一位贵妇。根据传说,为了让考文垂地区的民众得以减免她丈夫麦西亚伯爵施加的重税,她曾赤身裸体骑马穿过当地的街道。
《榆树》(得一忘二译)
给茹丝·芬莱特(1)
我了解那底部,她说。我用粗大的直根了解它:
它,是你所恐惧的。
我不怕它:我已去过。
你在我深处听到的可是大海,
以及它的不满?
或是虚空之声,是你的疯狂?
爱是一个影子。
你撒着谎,哭喊着穷追不舍。
听啊:它的蹄声。它已经跑开,像一匹马。
我也将彻夜这样奔腾,狂野地,
直到你的头化为石头,枕头化为一方小小的赛马场,
回响,回响。
或者,我应给你带来毒药的声音?
它现在化作雨了,这巨大的静寂。
这就是它的果实:锡白色,像砒霜。
我已饱经日落的暴行。
我红色的丝
烤焦到根部,燃烧,竖起,一只铁丝的手。
现在,我断成碎片,棍棒似地飞散出去。
如此暴力的风
不会容忍旁观:我必须尖叫。
月亮也绝不仁慈:她会拖住我,
残酷地,因为她不育。
她的辐射灼伤了我。或许,是我不放过她。
我放她走了。我放走了她,
萎缩了,干瘪了,像经过了彻底的手术。
你的恶梦占有了我,也馈赠我。
我被一种啼哭附了身。
它夜夜扑闪而出,
以它的钩爪,寻找值得一爱的东西。
这黑暗的东西睡在我的体内,
吓得我魂不附体;
我整天都感到它轻柔的羽毛似的转动,它的恶毒。
云朵飘过,云朵疏散。
那些一去不回的苍白,都是爱的面孔吗?
我心神不宁,是否因为这一切?
我无力承受更多知识。
这是什么,这张充满杀机
被树枝掐住的脸,是什么?──
它毒蛇的酸液嘶嘶响。
它僵化着意志。这些孤立的、迟缓的缺陷
能够致命,致命,致命。
注:
(1)茹丝·芬莱特(1931—),出生于美国、主要居住在英国的女诗人、翻译家。她是英国小说家艾伦·斯里托的妻子,普拉斯生前最后一年多的好友。
一、女性主义和普拉斯概述
女性主义是20世纪广泛兴起的在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反抗男权、争取女性自由的运动。长期受压抑的状态使广大女性在这场运动中奋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和身份,逐渐改变性别弱势的状况。这一运动的兴起,相伴着女性文学的兴起和繁盛。一大批文学巨擘先后涌现,一方面波伏娃,弗里丹等文学理论家已在文学史册上永绽光辉,另一方面,大量的女性作家和她们的文学作品也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理解甚至改变女性的生存状态。
普拉斯的诗属自白诗一列,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当普拉斯于1960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巨像及其他》时,读者和评论界反响并非十分热烈。到了1965年即她自杀后的第三年出版的诗集《爱丽尔》才开始为她赢得声誉。尔后由其丈夫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整理并出版了她的两卷诗集《渡湖》和《冬天的树》,把普拉斯作为自白派诗人的声誉推向了最高点。至今,她依旧声名不衰,尤其是1998年休斯的遗作《生日贺信》又再次勾起了人们对普拉斯深深的怀念之情。她的诗艺与人生悲剧无法分开。普拉斯不仅成为后现代主义自白派的代表,而且也因其作为女性作家为创作所做的努力和其诗歌中对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的碑石。
二、死亡作为抗争
西尔维娅·普拉斯在诗歌形式上继承了惠特曼的传统:简洁、大方、自由,没有雕琢的痕迹,好像是自然流淌出来的,但内容上别开生面,很少顾忌,残缺的肢体、肮脏的角落、恐怖的病房,都能借来入诗,又因为诗人是女性,其视角就更为独特,所选择的意象更为敏锐。尤其是普拉斯与丈夫分手后,内心一片茫然,“光明不复存在”,写出的诗越发刻薄,也越发深刻。
在普拉斯一生的诸多恶梦中,父亲像一座巨大的雕像投下了沉重的阴影,使她一生都为之负罪累累,痛苦不堪。普拉斯为逃避孤独曾经将父亲当作自己的偶像,但后来这个偶像反而变成了对她个人生活最大的威胁,全部人生信念从此崩溃。女性主义认为父权为中心的社会机制是女性受压抑的根源,因此,抗争父权或男权成为其不懈的动力和目标。在众多女性作家笔下,寻回话语权,找回女性意识,重置迷失的身份都是抗争的手段。普拉斯在其狂暴内心的指引下,描述了大量以死亡为意象的诗歌。虽然一方面评论家们一致将她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解释她笔下黑色艺术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女诗人从其女性角度出发对父权社会作出的反抗。
《爹爹》这首诗歌充斥着浓重的压抑气氛,她写到:“你是只黑皮鞋/我曾像只脚住在这里三十年/穷困和悲凄/只敢呼吸和抽泣。”诗人将她的父亲比作法西斯、魔鬼等,而诗人自己却以犹太人自喻,深刻地揭示了其成长环境的压抑状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进入父权社会后,女性在社会、家庭关系里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在性别权势中低于男性,长期受到男权社会的束缚。在普拉斯的诗作中,这类受压制、受束缚的状态透过其女性的独特体验,如分娩,对身份的转变感到惶恐不安,对新生儿的亲近与排斥,对父亲的复杂感情,对丈夫的爱恨交织等等。
然而,在诗中除了凝重的压抑感,读者仍能体味到诗人对父亲的爱和依恋。普拉斯将父亲比做法西斯,但却写到,“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那人(指其父) ,把我可爱的红心一咬两半//我十岁时他们埋葬了你//二十岁时我有死的意图/回到,回到,回到你的身边,哪怕你已变成白骨。”诗人甚至将自己和她父亲合为一体,“要是我杀一个人,就等于杀两个人”,从这些诗句中,普拉斯对其父亲的依恋清晰可辨。结合到诗人的经历,评论家也认为这种对父亲的复杂情感也是她对背叛自己的丈夫的感情写照。
正是这种爱恨交加、依赖和埋怨相间的感情,使女诗人在精神上愈加痛苦,受尽煎熬,最终进发了那撕心裂肺的呼喊,“爸爸,我要杀死你,/我来不及动手你就死去——/一尊可怖的雕像大理石般沉重。”诗中她还把父亲比作魔鬼、法西斯、希特勒,流露着嘲讽、反感、怜悯的复杂情感。在《爹爹》这首诗里,除了表现某种希望的破灭外,它也许不能单纯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父亲,而抽象延伸为一种象征失望、异化、邪恶、神秘、怨恨以及男女性别对立等诸种含义。普拉斯在这首诗里,一连也用了好几个“黑”字,“你站在黑板前面,……你是只黑皮鞋/……一身黑的男人,/……那架黑色的电话机被连根拔起/……你那肥厚的黑色心脏里有一根标桩/因而村民不喜欢你。”这几个黑字固然与她惯用的以黑色作为艺术底色有关,在看到普拉斯对希望破灭后的绝望和难以排遣的郁恨中,也让人看到了她对崇高和阳刚之美的彻底否定。
最终,诗人以死的志愿结束了这种精神的折磨。“爹爹,爹爹,你这混蛋,我结束。”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以死相抗,来显明自己抗争压抑、抗争父权的努力。
三、死亡作为妥协
普拉斯的诗显而易见具有某种类似于疯癫状态的狂躁气质,它们不仅有许许多多突兀的、出人意料而又光芒四射的意象和意味,难以穷尽的象征、隐喻,而且诗的语言也往往打破逻辑和时空的顺序、而随意识自由地驰骋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成为超越理性束缚和心理屏障的精神载体。她的意识在摆脱理性的限制而濒于疯狂之际,往往能直接洞穿生命的内核,论言妄语成为最灿烂夺目的诗章,就像在《女拿撒勒》中体现的那样,天才与疯狂悲剧性地统一在一起,令人惊叹又惋惜。
相较于《爹爹》,《女拿撒勒》这首诗以更加直白的方式讨论死亡。“死,是一种艺术,象一切其他的东西。”从该诗的最后一节来看,“我披着一头红发/从灰烬中升起,/象呼吸空气一样吃人,”该诗表达的是强烈的反抗意识。在经受了男权的压抑,诗人渴望通过死亡来摆脱这种痛苦,并进行最强烈的反抗“象呼吸空气一样吃人”。
当结合到诗人之前的叙述,诗人的渴望只能是其终极的幻想。首先呈现于读者眼前的是诗人对死亡的眷恋,“我又尝试了一次,/我十年/尝试一次——”,从中读出的是诗人曾经的自杀企图。接着“我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女人,/我仅仅三十岁,/我象猫一样有九条性命,//这是第三条/每十年就要消灭/一个废物!”此处进一步验证了诗人对生之厌恶。之后,普拉斯再一次提及之前的自杀经历。“第一次发生在十岁,那是一次意外,/第二次是我有意,要干出个明堂,/根本不愿回头。”
在诗歌中,死亡的意象也比比皆是,“纳粹的灯罩”、“镇纸”、“上等犹太人亚麻布”、“那条餐巾”等等。然而从这几句“我这样干使自己感到死是地狱/我这样干使自己感到真死,/我猜想你们会说我身负某种使命”,感到诗人隐隐地为着某种力量所折服。死亡是恐怖和真实的诗人自己明了,可她仍揣测着世人知道其死后的猜想,这似乎带给她某种满足感“身负某种使命”。仔细阅读诗歌,这种使诗人折服的力量来自诗中所指的“我的敌人”,“敌人先生”。“我的敌人”使诗人放弃生之希望,奔赴“某种使命”。
结合到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了摆脱对父亲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普拉斯曾有过几次自杀尝试。在丈夫背叛她另结新欢后,普拉斯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自杀,并最终离开人世。诗人试图摆脱父权的压抑,妄图以死相抗,可是最终成为一种向“敌人先生”妥协的方式?“我的敌人”强化了男女两性的对立,也让人们看到了诗人的妥协。
四、死亡的终结,不尽的猜想
普拉斯的诗歌穿梭于“自白、自我、自杀”之间,并将罗伯特·洛威尔所开创的一代诗风推到了顶点,实现了W·B·叶芝所谓的20世纪诗歌将是“心灵发出的叫喊”的夙愿。她是一个“内心狂暴的诗人”,她在用生命写诗,也在用死亡锻造黑色艺术。某种意义上说,她要通过诗的形式控告男性作为整体,在婚姻、家庭、社会上给女性造成的伤害。按照普拉斯的理解,女性因男性的压迫心理逐渐扭曲,原本完整的人格变得支离破碎。
通过《爹爹》、《女拿撒勒》两首诗歌中死亡主题的探究,普拉斯以死亡为武器来对抗男权社会,还是以死亡向男权社会妥协,都尽得剖析。最终诗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让人们不断地揣测诗人的死是抗争抑或妥协。
1、本站所有文本、信息、视频文件等,仅代表本站观点或作者本人观点,请网友谨慎参考使用。
2、本站信息均为作者提供和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
3、对任何由于使用本站内容而引起的诉讼、纠纷,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有侵犯你版权的,请来信(邮箱:baike52199@gmail.com)指出,核实后,本站将立即删除。
下一篇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上一篇 特德·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