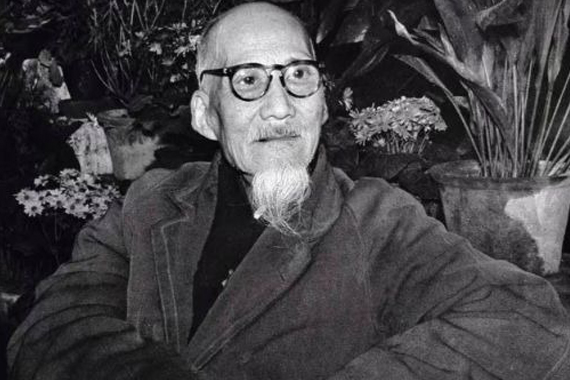-
国语·越语 编辑
《国语·越语》是我国第一部记言体国别史《国语》的第二十卷和第二十一卷,主要记述战国时期越国史事。
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执其手而与之谋。
遂使之行成于吴,曰:“寡君勾践乏无所使,使其下臣种,不敢彻声闻于天王,私于下执事曰: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
夫差将欲听与之成,子胥谏曰:“不可。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员闻之,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灭之。失此利也,虽悔之,必无及已。”
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国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
太宰嚭谏曰:“嚭闻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与之成而去之。
勾践说于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
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
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
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哺之也,无不歠也,必闻其名。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
国之父兄请曰:“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诸侯之国,今越国亦节矣,请报之。”勾践辞曰:“昔者之战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与知耻?请姑无庸战。”父兄又请曰:“越四封之内,亲吾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雠,其有敢不尽力者乎?请复战。”勾践既许之,乃致其众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
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众之不足也。今寡人将助天灭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也。进则思赏,退则思刑,如此则有常赏。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果行,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是故败吴于囿,又败之于没,又郊败之。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请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勾践对曰:“昔天以越予吴,而吴不受命;今天以吴予越,越可以无听天之命,而听君之令乎!吾请达王甬句东,吾与君为二君乎。”夫差对曰:“寡人礼先壹饭矣,君若不忘周室,而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愿也。君若曰:‘吾将残汝社稷,灭汝宗庙。’寡人请死,余何面目以视于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灭吴。
国语·卷二十一越语下
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王曰:“为三者,奈何?”对曰:“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不问,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王弗听。
范蠡进谏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无是贰言也,吾已断之矣!”果兴师而伐吴,战于五湖,不胜,栖于会稽。
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为之奈何?”范蠡对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曰:“与人奈何?”对曰:“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王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於吴,曰:“请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于大夫,随之以国家之重器。”吴人不许。大夫种来而复往,曰:“请委管龠属国家,以身随之,君王制之。”吴人许诺。王曰:“蠡为我守于国。”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王曰:“诺。”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
三年,而吴人遣之。归及至于国,王问于范蠡曰:“节事奈何?”对曰:“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
王曰:“不谷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后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种亦不如蠡也。”王曰:“诺。”令大夫种为之。
四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先人就世,不谷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则禽荒,入则酒荒。吾百姓之不图,唯舟与车。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吴人之那不谷,亦又甚焉。吾于与子谋之,其可乎?”对曰可:“未可也。蠡闻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
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蚤图。夫吴,君王之吴也,王若蚤图之,其事又将未可知也。”王曰:“诺。”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吴王淫于乐而忘其百姓,乱民功,逆天时;信谗喜优,憎辅远弼,圣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适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对曰:“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诺。”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闻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骤谏其王,王怒而杀之,其可乎?”对曰:“逆节萌生。天地未形,而先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杂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诺。”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今其祸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资财之不足以支长久也,彼将同其力,致其死,犹尚殆。王其且驰骋弋猎,无至禽荒;宫中之乐,无至酒荒;肆与大夫觞饮,无忘国常。彼其上将薄其德,民将尽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问焉,曰:“谚有之曰:‘觥饭不及壶飧。’今岁晚矣,子将奈何?”对曰:“微君王之言,臣故将谒之。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弗及。”王曰:“诺。”遂兴师伐吴,至于五湖。
吴人闻之,出而挑战,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许之。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臣闻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天节固然,唯谋不迁。”王曰:“诺。”弗许。
范蠡曰:“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用则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
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究。今其来也,刚强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诺。”弗与战。
居军三年,吴师自溃。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使王孙雒行成
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祸于吴,得罪与会稽。今君王其图不谷,不谷请复会稽之和。”王弗忍,欲许之。范蠡进谏曰:“臣闻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天节不远,五年复反,小凶则近,大凶则远。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则不远。’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王曰:“诺。”不许。
使者往而复来,辞愈卑,礼愈尊,王又欲许之。范蠡谏曰:“敦使我蚤朝而晏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夫十年谋之,一朝而弃之,其可乎?王姑勿许,其事将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许,而难对其使者,子其对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应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王孙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无助天为虐,助天为虐者不祥。’今吴稻蟹不遗种,子将助天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孙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鼋鼍鱼鳖之与处,而蛙黾之与同渚。余虽腼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孙雒曰:“子范子将助天为虐,助天为虐不祥。雒请反辞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执事之人矣。子往矣,无使执事之人得罪于子。”
使者辞反。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
反至五湖,范蠡辞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王曰:“不谷疑子之所谓者何也?”对曰:“臣闻之,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为此事也。今事已济矣,蠡请从会稽之罚。”王曰:“所不掩子之恶,扬子之美者,使其身无终没于越过。子听吾言,与子分国。
不听吾言,身死,妻子为戮。”范蠡对曰:“臣闻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
王命工以良金范蠡之状而朝礼之,浃日而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曰:“后世子孙,有敢侵蠡之地者,使无终没于越国,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
本文在卷上第一、七、十、十二四个段落中,相对集中地记载了越王句践在谋划雪耻过程中,几个关键时刻的若干精彩话语和几个重要场合里的一些巧妙辞令。围绕着句践的这些语辞,作者不仅质朴简练、主次分明地?述了越国自兵败于吴到兴兵灭吴的全过程,线索十分清楚,结构颇为谨严;而且,作者还注意把越王语辞的语境一一交代清楚,避免了单薄、枯燥,而显得丰厚、精彩。读者从全篇勾勒的背景、所渲染的气氛、所映衬的对象、所描述的行动中,来聆听、品味越王句践的“说”、“誓”、“辞”、“对”的具体内容,他那忍辱负重的顽强性格和体察民情的深入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本篇在写作上,其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所记之言与所言之事,主次清楚,融为有机的整体;二、所记之言范围广泛,层次丰富,作者史识相当卓越;三、所记之言生动形象,个性鲜明,如身临其境;四、所记之言发语巧妙,委婉得体,辞令优美、贴切。下面,仅就越王句践的语辞描写略加分析。
越王句践是本篇的中心人物,他的语辞是文中载录的重点。他在雪耻灭吴这一过程中的光辉形象主要是藉此得以显现、突出。句践在文中的五段语辞,每段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一开头的“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它同“述经?理”的“论”、判断是非真伪的“辨”,有所区别,一般只要求把问题说清楚即可,无需论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指出:“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员;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吴纳在《文章辨体‧说》类序中强调:“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句践的这段“说”辞,合乎规范,较为得体,力度极强。
他在败亡之际,火与血的教训促使他诚恳地作“自我批评”,主动向国人告罪。但意并不限此,主要目的在于“请更”(恳请变更、改革),即认真找出失败原因,果断地采取厉精图治的措施。这可以从越王在言说以后所落实的一系列葬死、问伤、养生以及卑事夫差等等行动中得到印证。“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这一说辞,生动形象,可见句践此时心情沉痛,语调哀婉,很容易打动国人的心弦,引起共呜。
第七段和第十段中各有两段“誓”辞。据徐师曾《文体明辨‧誓》 类序:“誓者,誓众之词也。蔡沈云:‘戒也。’军旅曰誓,古有誓师之词,…… 又有誓告草臣之词……又约信亦称誓…… ”,我们可以看出第二段中句践“致其父母昆弟而誓”,显然是“誓告草臣之词”,兼具“约信”性质。这段誓词,既生动形象(“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 ,又颇具个性色彩,“将帅……以蕃”这句话中的“帅”字兼有“统帅”、“表率”两层涵义,文中交代句践是如言履行、忠实践约的,这正是他的可贵、可敬之处。第十段中的“誓”辞,是国人一再请战、句践许战以后、越国将士秣马厉兵、整装待发之前的“誓师之词”。在这段“誓”里,既有敌我双方形势的冷静分析,又有吴越两国兵力的优劣比较,更有志行知耻的强调和“常赏”、“常刑”的号令,还有“助天灭之”的鼓动,写得理正词严,情盛语壮,显示了凌云的豪气和必胜的声势。
如果说,前面评析的“说”和“誓”都是越王句践主动发出,经过精心准备之后才予以颁布而公之于众,那么,第十段中对国之父兄请战的“辞”谢和第四段中对吴王夫差求和的“对”答,则是他临场发挥,即兴说出,从中更可以见出句践的思想和为人。他内心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从其它史籍中记载的“卧薪尝胆”等等情节中可见一斑),忍辱负重、力图兴兵、蓄意灭吴,但在这两个重要场合中,“辞”、“答”的话语却都表现得那么谦卑从容、婉转动听,不失一国君主和一代霸主的气度和心胸。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巧妙措辞,相反相成,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有力地刻画出句践深谋远虑、外柔内刚等性格特征,我们越仔细咀嚼,越觉得饶有兴味。
1、本站所有文本、信息、视频文件等,仅代表本站观点或作者本人观点,请网友谨慎参考使用。
2、本站信息均为作者提供和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
3、对任何由于使用本站内容而引起的诉讼、纠纷,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有侵犯你版权的,请来信(邮箱:baike52199@gmail.com)指出,核实后,本站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