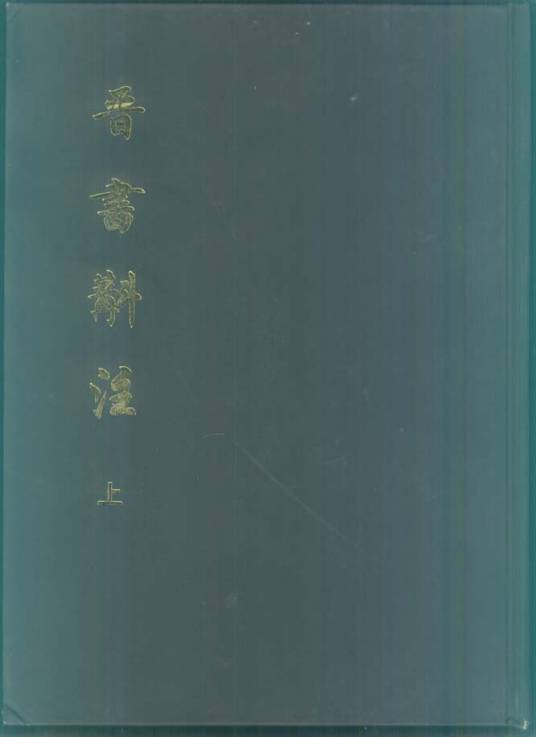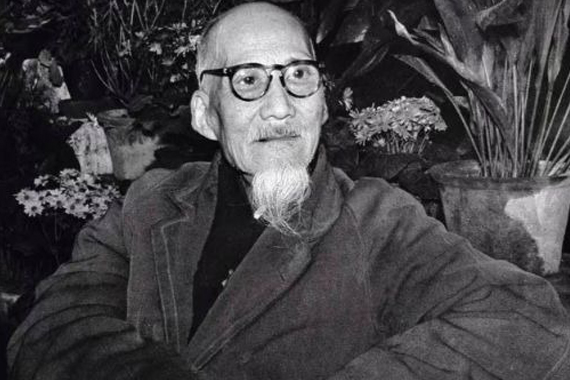-
晋书斠注 编辑
《晋书斠注》,是一种著名的《晋书》史注,比较全面地利用了20世纪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共一百三十卷,由吴士鉴、刘承干合注。作为一部著名的史注,《斠注》在形式上是传统的,但在学术思想上却是现代的,他们广泛利用了20世纪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吸收了王国维、罗振玉及梁启超等人的学术成果,包括域外的一些相关史料,带有史注在思想方法上新旧交替的特点。 对唐修《晋书》的史源、正误等,进行了广泛的考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述十个方面可以归并为三大类,第一类溯源,是关于史源问题。第二类捃逸、削繁、表微、补阙,是关于材料问题。第三类辨例、正误、考异、广证、存疑,是关于是非问题。既往的学术研究,多是从这三大类十个方面寻求这种史注体著作的文献学意义,却忽略了它们在史学史上的积极价值,从而漠视了这种重要的史学存在。而研究史注的成就,即从史注中透析出注史者的史学思想、史注与史学的关系及其成就,正是我们所应努力的方向。
所谓历史公案,通常是指在历史上有争议的历史事件,或者至少在当时有重大争议而往往被后世忽略的事件,也可以指当时很清楚而被后人遗忘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又是应该弄清楚的。而对于这一类工作,过去一般的史注多是采取含糊其辞或回避的态度。
以下分别以几个例子来说明《斠注》中的情况。
其一,关于《论语集解》的作者问题。《论语集解》一书在儒学与魏晋玄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不言而喻。后世学者每言何晏《论语集解》,似乎没有异议,即便少数人知道该书的著作权并不专属何晏,但约定俗成,也并没有对此提出置疑。殊不知这个著作权问题,涉及到对当时儒学与玄学整体的认知和评价,并非小问题。《郑冲传》记述郑冲和孙邕、曹羲、荀顗、何晏共五人“集《论语》诸家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从《论语集解·序》中也可以看出,这篇《序》就是《晋书》的史源所在,作者也是五人,而且署名次序和《晋书》极为接近。清朝四库馆臣发现,陆德明《经典释文》于《学而第一》下注解道“一本作‘何晏集解’。”在《序录》中又说“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斠注》的作者经过考察,发现问题恰恰出在隋唐之际。《隋书·经籍志》载“《集解论语》十卷,何晏集”,大约受唐人这一记述的影响,两《唐书·志》也均作“何晏《集解》”。只有《宋志》正确地把作者表述为“何晏等”。……从这一历史问题的提出,到历叙各代变化,从详列具体资料,到引出读者的思考,并大致可以推断结论从而解决问题,完全是《斠注》给人们提供的。
其二,关于“寒食散”资料的考释和评述。……《斠注》于此补充大量材料,约可分为以下几项:一是其他人服食寒食散的情况。这里补充了服了寒食散之后“性与之忤”的皇甫谧、由于没有太医令照顾而“药数动发”的魏太祖;二是有关寒食散的医药论著。计有皇甫谧的《论寒食散方》、东平王徽之子曹翕所撰《解寒食散方》、释道洪《寒食散对疗》等十种,并提及唐代的《外台秘要》和《千金翼方》还保留其法;三是有关寒食散的文学作品。提示《艺文类聚》引有嵇含的《寒食散赋》;四是寒食散的成份、服后的感觉及寒食散的发展。《斠注》先后征引了《世说·言语篇》及刘孝标《注》,言其主要是“精刚内蕴,符采外标”的丹沙、雄黄、云母、钟乳、石英之类,不仅能治病,也给人一种“神明开朗”的感觉。出自汉代,但当时服用的人很少,史言何晏首获神效,因此大行。五是校注者的基本态度。对于寒食散,校注者认为:“本避伤寒卒病法也,士大夫不问疾否服之为风流,则始于何晏。魏晋人服散,至死不悟。窭人子弟饥寒致病,谬云散发,其时以为笑谑。”通过《斠注》的一番阐释,使人们弄清了流行于中古漫长时期的寒食散问题。对于今人的文化史研究而言,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从这段史注中也可以看出,史注作为一种史体,其本身的扩展性是很大的,一则取决于注者的观念,二则取决于注者的驾驭能力。
……
二、突破传统界限,扩大注史范围
旧有的史籍注释,多是侧重在史籍的某一方面,或音义、或字词、或地理、或典故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特色,满足了读者的部分需要,但总是在另一些方面难以尽如人意。大约多是受前人经注中“疏不破注”的影响,从而限制了史注的应用范围。《斠注》的注释却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补充原著阙略、汇集历史上的研究成果等方面,有自己的突出特点。我们可以从几个事例考察《斠注》的作法。
其一,以补阙为手段从而扩大历史记述的含量。《晋书·孙统传》称孙绰在当时文士中为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斠注》于此引用了叶昌炽《语石》中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观点表述道:魏武帝时以天下凋敝禁立碑,直到魏末禁忌尚严。晋武帝时又以“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切禁断。直到安帝时,尚书祠部郎裴松之又议禁断,可见虽然“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然大臣长吏人皆私立。”法令虽严,胆大的照干不误,本《传》就是明证。校注者又引证了《艺文类聚》所引孙绰撰《丞相王导碑》、《太宰郗鉴碑》、《太尉庾亮碑》、《司空庾冰碑》等,从而使《传》中的这段记述更为可信,也使读者知道任何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和联系。可以说,无形中这也是注者史学方法论的一种展示;另一个颇有特色的例子在《晋书·陶璜传》,传主在奏言中称“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然而,尽管官府禁断甚严,民众为了求生存就不得不想出各种对付办法。《斠注》引征了《太平御览》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合浦有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采,巧盗者蹲水底破蜯得好珠,吞之而出。”合浦在孙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曾一度改名为珠官郡,是著名的珍珠产地,因此这段材料是再典型不过的了。《斠注》就是这样,把立禁与犯禁的材料列在一起,使读者窥见法令与习俗、公开与私下、官方与民间在社会不同状态下的巨大差异,这样无疑会加深人们对当时社会历史的认识。
其二,通过补充材料,使抽象的历史鲜活起来。《晋书·羊琇传》记述这位外戚生活豪侈,“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洛下豪贵咸竞效之。”历来读《晋书》者对“屑炭和作兽形”多不详究,或想像是把炭末做成兽形,颇为好看,甚至有理解为洛阳当地没有大树烧炭而采取的因地制宜的方法。《斠注》引《御览》卷四九三《晋朝杂记》并参卷八七一《语林》给读者描述了这种情景,即当地木炭像粟,捣小炭为屑,然后以物和之作兽形,用以温酒。在火势最旺的时候,这些炭屑做的小兽都张开口向着人吐火,赫赫然一幅骇人的情景。可见,除了很好看以外,也很生动,不然不会使“洛下豪贵咸竞效之。”通过对详情和细节的记述,不仅使读者加深了对当时上流社会奢侈习性的认识,而且使读者知道简单的历史表象背后还可以有更深的读解。
三、继承前人观点,发现学术规律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二一中提出“译音无定字”的观点,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古史领域涉及到少数民族和域外人名地名问题。诸如“蝚蠕”、“柔然”、“蠕蠕”、“芮芮”、“茹茹”,其实一也,明白了“译音无定字”的道理,人们再也不会为这些字的不同而争论不休了。《斠注》的作者领会了钱氏这一观点,并在具体的校注实践中予以应用,而且不仅如此,还对这一观点发扬光大,使之更加充实。如在《晋书·秃发傉檀载记》中注解“折掘氏”即《广韵》十七中的“折屈氏”,“屈”为“掘”的省文,其观点为“虏语无定字”。和“译音无定字”相比较,这一观点的涵盖性显然更广一些。因为它不仅指字音,也指字形,同时也不排斥指字义。不仅如此,还提出“童谣无正字”的观点,这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明确到了这一点,就会对古籍谣谚中的字词差异予以正确的理解和处理。古籍整理和阐释的理论,就是这样在继承中而得到发展的。
注者常能够以小见大,从字词或文献知识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可分为几
种情况:
一是归纳文字错讹规律。以往的史注中对于文字的考证,多是简单地给出结论,使读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斠注》的考证完全不是这样。《晋书·桓玄传》中有“广武将军郭弥”,而《世说·贤媛篇·注》引《续晋阳秋》“郭弥”却作“郭珍”。何者为是?《斠注》的作者用自己广博的校勘经验和文字学知识,明白地指出“弥”有时写作“弥”,容易误作“珎”,而“珎”又可以写作“珍”,实乃“珍”之异体,这种由“弥”到“珍”讹误的演变是明显的,在古籍中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珍”却不能逆演变为“弥”,因此他们的观点是错在《续晋阳秋》。
二是应用文字知识推定史实。《刘颂传》言传主“病卒”,《通鉴·晋纪考异》引《三十国春秋》认为刘颂是在统治者内部斗争中自杀,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斠注》指出:“案以下文‘谥曰贞’证之,颂之死必是自杀。当时讳言之,故云‘病卒’。《三十国春秋》乃是实录。”变歧异为定论,而且这种随手拈来的论证技巧令人欣赏。
三是利用避讳知识考察史料。一种情况是指出避讳未尽的地方,间接地反映唐代史臣的疏忽。在为《李胤传》做注解时,《斠注》的作者发现《御览》卷四一二引王隐《晋书》“李胤”作“李彻”,便指出宋人避讳改“胤”为“彻”,在同卷注者又有新的发现,即为避讳宋人又改“胤”为“允”。由此看来,避讳的情况很复杂,不是简单的字与字的对应所能解决问题的。避讳学的知识和经验就是这样不断积累起来的,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即每点明一个朝代的避讳痕迹,就表明这段史料是经过该朝代梳理过的,在使人们增加历史沧桑感的同时,也使人们知道在解开了一些避讳的谜团之后,说不定还会有更多地谜团在等着人们。
四、难以避免的不足和不应有的失误
像一切著作一样,《斠注》也有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这里条列数则以见一斑,以供今人在为古籍史著作注时引为教训。
其一,校注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及不应有的错误。涉及到《晋书》中“郗鉴”与“郤诜”之姓的不同,后人多不甚了了,《斠注》完全采录并接受钱大昕的观点:即汉隶之后“郤”同“郄”,“与从希之郗音义全别”,最后确定清楚,望出河南济阴者为“郤”,读如隙,望出山阳高平者为“郗”,读如“絺”。《斠注》在校注过程中,也利用这一学术成果校正了一些错误。
其二,让神异迷信之事充斥在史注中。历史上人们对唐修《晋书》采用《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书的材料颇多微词,尽管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后世学者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然而《斠注》却一方面讥弹唐修《晋书》采录神怪迷信,另一方面自己却在注释过程中大量增广这些内容,形成了极为矛盾的注释思想和不协调的风格。《晋书·庾冰传》记载郭璞为庾冰卜筮之事,仅言“子孙必有大祸”一语,《斠注》则不厌其烦征引《太平寰宇记》中有关这次卜筮的细节,又用种种物异现象来证明“璞卜皆验也。”还有的《晋书》原文没有一点迷信成分,但《斠注》却大肆补充这种内容,如《蔡谟传》仅言蔡谟卒,“时年七十六”,《斠注》便在下文引了《太平广记》卷中的《灵异志》,言传主生前曾在亦真亦幻中见到鬼魂,预示到了自己的命运等。这种对鬼神世界的兴趣远远超过唐代史臣。假如说可以原谅唐人修《晋书》多采小说传说是不得已的话,因为他们所依据的史料中本来就充满着这些东西,他们无法抛弃前人的文化积淀,更无法克服魏晋人所赖以生存的神异气氛,然而到了20世纪校注者居然还要欣赏这些东西,让人难以理解,甚至完全可以视为倒退。
其三,有误解传统史学精蕴的地方。在《晋书·苻丕苻登载记》末的“史臣曰”中,唐史臣基本上袭用了前人的观点,对少数民族建立的苻秦王朝评价不高。《斠注》的作者也赞成这一观点,但同时又引了《洛阳伽蓝记》中关于评价苻生的一段话。说:“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然而《斠注》的作者不了解这一点,却显示出了考据者的拘泥,他们认为赵逸其人的来历十分可疑,“其言荒诞,恐不足信。惟以其为六朝人之言,故采之以备异说。然与《载记》所言苻生淫暴诸事判若两人,似未为实录也。”虽然也承认可备异说,但最终还是不相信其真实性,不能不说校注者是受正统史观的偏见和“正史”的官方权威的双重影响所致。
1、本站所有文本、信息、视频文件等,仅代表本站观点或作者本人观点,请网友谨慎参考使用。
2、本站信息均为作者提供和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
3、对任何由于使用本站内容而引起的诉讼、纠纷,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有侵犯你版权的,请来信(邮箱:baike52199@gmail.com)指出,核实后,本站将立即删除。